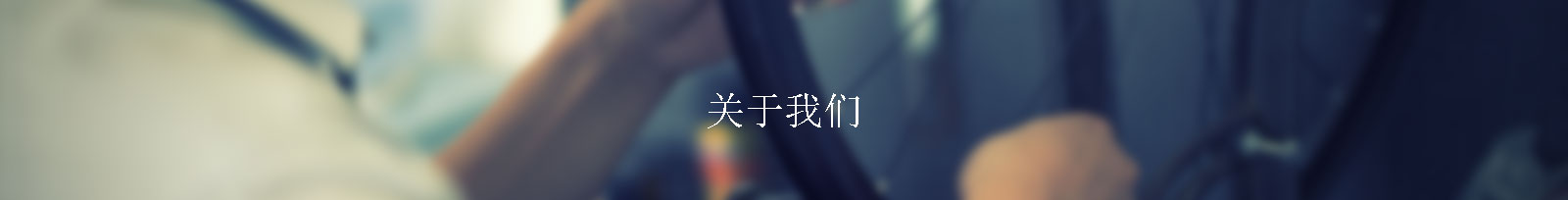发布时间:2022-10-02 14:19:31
《妈妈!》,原名字叫《春歌》。
这是杨荔钠导演的第三部剧情长片,前两部分别是《春梦》和《春潮》——三部电影合在一起,被媒体称为“女性三部曲”。
就像前两部作品,杨荔钠再次把镜头对准家庭关系,或者说母女关系的内部,用一个个极其生活化的现实场景,戳穿亲情背后的冰冷与阵痛。
杨荔钠的语法
POST WAVE FILM
先说杨荔钠,和她的电影语法。
在中国的女导演群体里,杨荔钠是比较特殊的一个。
她最开始是一个舞蹈演员,然后在贾樟柯导演的《站台》里,扮演女二号钟萍。
《站台》里的杨荔钠(右二),图源:杨荔钠微博
之后她又转行做导演,是中国第一位独立纪录片女导演。
1999年拍摄的国内首部DV影像纪录片《老头》(1999),斩获“日本山形纪录片电影节”亚洲新浪潮优秀奖之后,又拿下“巴黎真实电影节”评委会奖,还在2001年一举拿下了“德国莱比锡纪录片电影节”的金奖和观众奖。
凭纪录片扬名国际后,她不再满足于客观记录,转行做剧情片导演,于是就有了让李安导演盛赞不已的《春梦》(2013),以及后续联手郝蕾的《春潮》(2019),和现在这部改名叫《妈妈!》的《春歌》。
与纪录片的客观真实不同,杨荔钠的剧情长片变得极其私密。
那是一个只有女性才能有更深刻体会的电影世界——男性当然也能理解,但天然的性别差异,还是会让这种审视带有一定的理解障碍。
德国小钢炮这就让杨荔钠那些贴着现实主义标签的题材,显出非现实的意趣。
比如,杨荔钠极其喜欢用荒芜丛生的自然生物和环境,来喻指女性落败残破的身份和心境。
在《春潮》里,当金燕玲扮演的母亲,醉酒后仪态全失地辱骂郝蕾扮演的女儿郭建波时,不堪其辱的郭建波并没有直接反击,她只是躲在房间里,死命地抓住床头柜上的仙人掌,任由仙人掌刺破自己的手。
这种写实的部分还好理解,无非是在用指尖之痛,把郭建波的内心伤痛外化。
但杨荔钠通常会随着故事推进,用更加呓语的方式,来穿插自然物象既让故事变得跳脱,又增加人物情绪上的捉摸不定。
就像扮演外孙女的曲隽希,被迫周旋在强势的外婆和沉默的母亲中间左右为难时,屋里突然出现了一直粉色的鸽子;还有郝蕾被母亲金燕玲无故刁难时,她梦见母亲变成一只手脚被捆住的黑羊,被一群精神病院的护工给抬走。
《春潮》(2019)
类似情况也出现在《春梦》和《妈妈!》里,比如《春梦》里养在鱼缸里的金鱼,和《妈妈!》里被扔在餐桌上的,已经被从土里拔出来的花株。
《春梦》(2013)
这些意象游离在现实和虚妄之间,以失去了原本自然状态的姿态,沦为受人类奴役的意涵,喻指的就是人物在亲情关系里,被折磨得体无完肤的样子。
尽管这些东西和镜头一闪而过,却在杨荔钠的叙事里,变得意犹未尽。它们就像杨荔钠镜头里无处不在的水一样,尽管沉默不语、一闪而过,却始终言有所指、分量十足。
比如《春梦》里的女主角方蕾,做了四次与意中人交欢的梦,每一次都有水:
第一次是水滴的声音,第二次是在水中缠绵,第三次则波涛汹涌,第四次再回到水滴的声音——这些水的意向,由小到大地循环一圈,昭示着身为女性的方蕾的情欲,从复苏到挣扎再到自洽的过程。
《春梦》(2013)
《春潮》则更直接、更露骨。
郭建波在不同的男人身上放纵情欲,本质就是为了对抗母亲:她就是要自暴自弃中,活成母亲不喜欢的样子——这时的水,是带着气雾的、溅起水花的,喻指的就是那种报复、放肆与泛滥。
但当母亲陷入昏迷,彻底失去对她的掌控,她选择与盲人按摩师纵情欢爱,第一次把性欲当成性欲本身,而不是对抗母亲的工具,从中获得了纯粹的女性欲望的满足——这时的水,从两人脚下喷涌而出,蓬勃有力,喻指的是郭建波澎湃且纯粹的情欲。
《春潮》德国小钢炮说明书(2019)
《妈妈!》里也有很多水的意象。
不同的是,《妈妈!》里的水的意向,不再是《春潮》里的情欲那么露骨,而是成了奚美娟那个角色内在情绪的代言人。
最开始,吴彦姝扮演的母亲,指责奚美娟扮演的女儿这辈子浪费了太多水,其实就是在压制她的情绪。所以俩人吃饭时,吴彦姝一脸怪笑地侧着耳朵去看女儿,暗示她水龙头没有拧紧,有滴答的落水声。
这种控制开始失效的第一个表现,发生在奚美娟确诊患有阿尔兹海默症之前,她毫无征兆地发病,忘记自己是谁、在哪里、做什么——镜头就在水下往上探,漂浮不定地记录着她的惶恐不安。
病情确诊后,有一场下雨的戏份:奚美娟在雨里手舞足蹈,把吴彦姝拿来的伞都扔掉,也要享受雨落身上的快意——让这种控制再也没有价值的那场戏,是俩人从大学回到家,奚美娟着急小便却打不开门,等吴彦姝砸窗开门,女儿已经尿一裤子。
所以,随着女儿病情越来越重,我们既能在她的幻象里,看到她躺在湖泊的小船上,又能在故事结尾,看到她和母亲嬉戏在大海边。
原本被压抑的,全都得到了释放。
这就是为什么说杨荔钠特别的一个重要原因:她极其擅长用最日常的自然意象,去反衬女人丰富又强烈的内在情感。
这些时候是不需要台词的。或者说,杨荔钠镜头里,那些充斥着非现实的自然物象的时刻,远远比她们用言语来表达自己的时刻,更饱满也更动人。
缺席的父亲
POST WAVE FILM
说回《妈妈!》。
显而易见,这部电影依旧保持着杨荔钠的个性特征,它仍然是个围绕家庭关系来展开的故事。
奚美娟扮演的65岁女儿终生未婚,结束大学教职生涯后,闲暇时到处做义工,回到家再照顾85岁的母亲吴彦姝;
当母亲发现女儿患有阿尔兹海默症,俩人逐渐调换照顾与被照顾的身份,并随着奚美娟病 情的不断加重,俩人爆发出越来越强烈的戏剧冲突。
杨荔钠安排了一明一暗两条线来推动剧情。
明线是奚美娟从无到有、从小到大的病情,这个过程从表面上主导着母女二人的身份变化;暗线则是奚美娟对父亲的情感,最开始是缅怀的、追忆的、留恋的,但随着她发病说自己“杀了人、但没用刀”的时候,观众才头皮一麻地反应过来——
原来这是一个类似于老舍挨完批斗回家,但没人给他开门,之后就心灰意冷投湖自尽的故事。
这就很有必要提到杨荔钠的另一个电影特征:缺席的父亲。
在很多女性题材的作品里,“缺席的父亲”往往用来指代男性存在造成的失衡,它们更多是批判性的,鞭挞的就是男权文化对女性造成的伤害,这种处理通常尖锐又犀利,极具刺破性。
但杨荔钠不是,或者说不全是。
她当然也希望能把女性从被侮辱与被伤害的社会性别中解放出来。
所以《春梦》里,女主方蕾闺密的老公常年在外寻花问柳,是一个不值得依赖的男人;健身教练与酒店男公关围绕在方蕾闺密的身旁,争前恐后地向她表达爱慕之情,实则是觊觎她口袋里的钞票。
《春梦》(2013)
到了《春潮》里,女主郭建波的闺蜜,因为无法生育被丈夫嫌弃,在他看来,不孕的女性对男人来说是没价值的,甚至是晦气和不吉利的; 至于疯狂追求郭建波的郝主任,登门拜访得知她“缺少一只乳房”时,脸色骤变、落荒而逃。
男人的虚伪和自私,被杨荔钠再现得淋漓尽致。
但难能可贵的是,杨荔钠从来不矫枉过正。或者说,杨荔钠从来不会为了追求女性主义的政治正确,就一杆子把男人全部打翻在地,而是通过两性对话的方式,来呈现多面立体的两性形象,试图对女性的身体和身份再赋义。
所以在《春潮》里,女主郭建波母亲的再婚对象,就是个通情达理且热情大方的贴心男,不仅无微不至地照顾着祖孙三代人的日常生活,还起到促进郭建波母女和解的积极作用。
反倒是郭建波和母亲,她们不仅不是好妈妈,而且还在以各自的方式戕害彼此。郭建波反抗母亲的那些沉沦方式,并不只是对母亲强势的抗争,更关键的根底出现在剧情暗示里——
特殊年代时,母亲很可能为了自己的前途,揭发检举自己的丈夫、女儿的父亲,最终导致他的死亡/缺席。
这就解释清楚了郭建波为何如此极端,却又如此沉默寡言:极端放纵是为了对抗,沉默寡言是因为不想撕破脸。
这个问题同样出现在《妈妈!》里,不同点在于:害死父亲的动作似乎全部由女儿发起,母亲在这件事上反而是缺席的。
在这里,杨荔钠留下了足够大的灰色空间,给观众去驰骋想象。
但她并不是没有留下任何线索,否则女儿也不会在病但未全病的时刻,对母亲说出如此清醒的回忆,更不会在这个阶段,对母亲接二连三地发脾气。
这就像不少酒品很差的酒鬼,总是喜欢借酒遮丑一样:他们并没有醉,只是需要一个幌子为自己失态的言行找一个台阶罢了。
当然,杨荔钠或许也有另一层考虑,那就是电影德国小钢炮说明书必须走进院线,跟更多观众见面:如果给了那么多温暖感人的瞬间,可背后却有个如此黑暗的事实,那大众是不是能接受得住?
毕竟,温暖与感动是万能的,但痛苦和真相却未必。
作者丨苗子
真味只是淡,至人只是常
豆瓣8.7,它为什么是近两年最好的纪录片?
详 细 课 程 介 绍 | 专 业 干 货 分 享
影 视 课 程 大 礼 包免 ! 费 ! 领 !
上一篇: 德国小钢炮:润肺止咳的水果都有什么
下一篇: 猫脸老太太这件事绝非小事,事件发生在一开始这个谣言是怎么起来